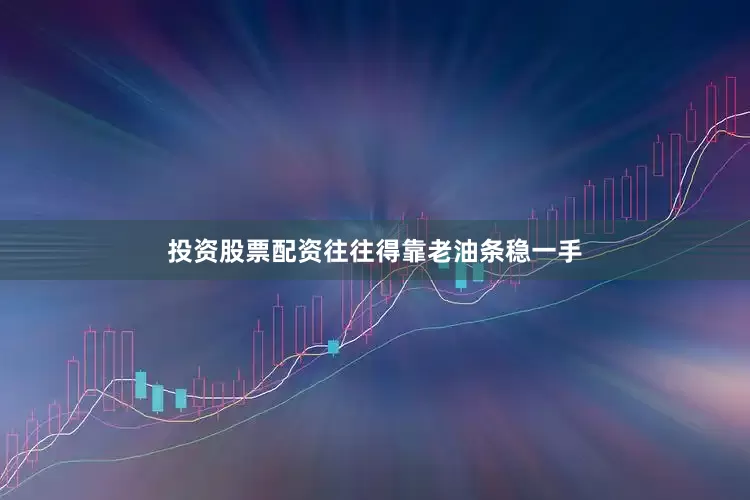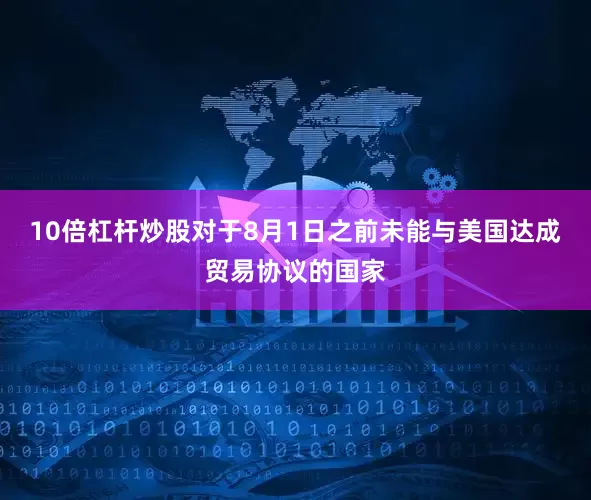【“爱国老人”马相伯,好像一开始被人们认识,就是一位“人瑞”了。学生于右任曾撰文说,马相伯“一生之盛业鸿烈,且多在中年以后,常人所指为桑榆暮景之时。”上世纪30年代初,在报刊、电台为抗日救国呼号的马相伯,已年过九旬,留给社会大众的印象,仿佛一个世外高人。而实际上,在德高望重的“期颐叟”形象之外,马相伯早年醉心科学、积极投身晚清的洋务与外交,创办震旦学院、复旦公学,参加辛亥光复之役,主持修订天坛宪草,力图以所学事奉更多人群。近日,在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,《马相伯年谱长编》出版,本报记者采访了编撰者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,请他谈谈马相伯的个性与成就,以及年谱长编如何编就。】
马相伯(1840—1939),江苏丹阳人,名建常,后改名良,字相伯。
“我学法语,非为法国用,是为中国用”
文汇报:1931年,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马相伯改变自八十岁后“不问世事”、一心著述的态度,积极宣传抗日。您在今年上海书展的新书发布会上提到,他甚至开始卖字救国,据说后来捐了一架飞机。可否介绍一下经过?
展开剩余89%李天纲:马相伯是七十岁开始习书画的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马相伯和章太炎发表“二老通电”,支持马占山,声援东北抗战,写下“还我河山”。救国会“七君子”事件时他也发起声援。马相伯对抗战的认识,是基于他对整个中国命运的理解,他个人在洋务运动后、在战场上的浮沉,以及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出发的。然而,在责任感背后,马相伯其实还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状态。
他还有一幅字“与造物游”,我觉得可以和“还我河山”配为对联。他以出世的态度从事入世的爱国救国,对人类、民族和个人都有完整的体恤。在一百多年的战乱中,他既渴望人类之间的永久和平,又站在公理和正义一边,主张抗战。
马相伯书《还我河山》(1932)和《与造物游》(约1935)
马相伯七十到一百岁一直在写对联,也有字画。由于年龄太大、笔力不够,他的书法写出来好像没那么成熟,实际上他练习碑体,相当有功底。他以卖字的形式为抗战募捐,3块、5块也写,20块也写。教会用5万元捐了二架救护飞机,马相伯和他的家族至少捐了半架。孙女马玉章回忆说,爷爷整天都在奋笔疾书。马相伯1909年以后还练习国画,于右任六十寿辰时他画赠《秋收图》,有时他们两人书画同署。马相伯的国学很好,与西学的根底同样深厚。顺便说,《马氏文通》出版后,国学圈子都是一片赞叹,说是中西文学被本书凿通了。
文汇报:但我们看到的《马氏文通》,署名是他的弟弟马建忠?
李天纲:这是一个争议。《马氏文通》现在署名马建忠,但是我做完年谱后有把握说马相伯一定是参与本书著述的。马相伯自己的说法是,因为弟弟名声更大,在家里也更受宠爱,才华也比他显扬,他帮忙一起整理了以后,是让马建忠一人署名的。我猜想,这部书不是《建忠文通》《眉叔文通》(马建忠字眉叔),而称《马氏文通》,可能也有这个原因,意为包含了马氏兄弟的共同贡献。
《马氏文通》是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文言文语法著作。马相伯在国学方面的功底比马建忠更好。马相伯年长,先入徐汇公学,马建忠晚进来,两人同住一房间。后来马相伯做公学的掌院,相当于教务长,他的意大利老师晁德蒞让他负责教国文和经学。徐汇公学的办学目标里也是要考科举的,四书五经是基本课。他们请了上海的举人、进士来教,短短几十年就出了有名有姓的秀才82个。另外,比较聪明的孩子像马相伯、李问渔就进入修院教育系统,学拉丁文、法文、英文,兼研究四书五经。马相伯是1847年徐家汇有中西会通学问后的第一批读书人。
文汇报:《年谱长编》中摘录了马相伯当时的一些谈话,十分生动。如“人但知日本谋我,罔知日人知我。谋我固可忧,而知我则更可惧”,呼吁加紧日本研究;1932年国联李顿调查团来,还托人告诉顾维钧要据理力争,“千万勿要叫我们江苏人坍台”。马相伯一生都在民族国家内忧外患中度过,您能给我们讲讲他一生的思想理路吗?他晚年时有人说他“好好先生”,他的真实个性是怎样的?
李天纲:马相伯曾说自己“少年最爱科学,晚年专心哲学”。1851年他来到上海徐汇公学念书,1862年的时候,开始痴迷于数学和天文学。他说那时候“几乎发了狂”,晚上睡在蚊帐里,睁眼闭眼间都在冒金星,好像看到数字在乱飞。他还写了120多卷的《度数大全》。我觉得那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精神危机了,这次精神危机导致了他离开教会。
他从小受的训练就是事奉人群、事奉社会,所以出世精神很强,没有功利态度,也没想着要到外面去赚钱或者做官。那为什么36岁突然离开徐家汇了呢?因为当时有这样的机会,大哥马建勋已经把马建忠介绍给李鸿章协办洋务。总理衙门发现这样懂英、法、拉丁、希腊文的人才在全中国找不到几个。而这样的人上海还有一个,就是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。马氏兄弟去李鸿章那里当幕僚的最重要的动机,还是认为在外面的天地更能够为国家做事。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沈葆桢都到徐家汇、董家渡来参观,可能就是这些接待激发了马氏兄弟对国家的责任感。
马相伯曾表示“我学法语,非为法国用,是为中国用”。这个说法非常真切。他说徐家汇是学法文的地方,法租界是用法文的地方,徐家汇的会士是看不起公董局商人的,他们是文化人。马相伯的自我期许很高,要做事必须是文化的事,为国家做,于是他在1876年时就从徐家汇出来了。
洋务运动轰轰烈烈,马氏兄弟希望帮助清朝往现代化发展,但很多事情没有做成。马相伯可能是最早上书建议修铁路的。另外,马氏兄弟在1887年就想办银行,马相伯专门去美国跑了一趟筹款,说好了5000万元办华美银行,中途却接到电报,说总理衙门不批了。之后他就自己去欧洲看了牛津、剑桥,考察教育。我认为马相伯萌发在中国办大学的愿望与此行有关。
马家早年在永安街开店,赚了很多钱,不用为钱发愁,还买了很多地。父亲、大哥去世后,马相伯、马建忠接手这些家产。但两人都是书生,都不会做生意。马氏兄弟做事情的时候,态度都是比较超然的。后来创办震旦,马相伯名下的这些地也都捐掉了,就是后来大家常说到的,“毁家兴学”。
“大学者……乃以学生有高等之程度及高尚之道德而大”
文汇报:马相伯曾任徐汇公学校长,之后因南洋公学事变创办震旦学院,又创办复旦公学,后来还出任北京大学校长,筹建辅仁大学,可以说他与几所重要的学校都有过从或渊源。他为震旦、复旦制定“崇尚科学、注重文艺、不谈教理”的方针;热心职业教育、女子教育。能否为我们谈谈作为教育家的马相伯?
李天纲:马相伯也是逐渐被推到高等教育的第一线的。他很早就意识到科举制不行了——不是说考试制度不行,而是教学内容必须结合现代知识体系,但是像数理化这些科目甚至都没有人教。原先总理衙门还想改造科举制,如上海的广方言馆、龙门书院、中西、格致就是办新学的;1901年,总理衙门聘了蔡元培主持南洋公学特班,专门培养师资,准备废科举。蔡元培就来请教马相伯。这时候马相伯已经六、七十岁了。
马相伯对教育是有感悟有理解的。他的教育思想跟徐光启一脉相承,就是会通。他们认为要理解西学,是需要中国的知识功底的。当年徐光启就说:“欲求超胜,必须会通;会通之前,先须翻译。”翻译就是跨了两个文化体系,要有两边的知识。
当时有一批人向马氏兄弟学拉丁文,这就要说到严复。严复曾写信给梁启超说,不要以为我的西学好,我的西学只是现在英国人讲的一些学问。严复翻译的约翰·穆勒《论自由》、甄克思《社会通诠》、孟德斯鸠《法意》都是18、19世纪英法的政治学、伦理学。严复说我的学问都是这些,马氏兄弟的学问才是欧洲学问的源头,也就是古典哲学。
梁启超是一个比较勤奋谦虚的人,他就盯着马相伯、马建忠学拉丁文。1896年,梁启超从北京到上海办《时务报》,就借住在马氏兄弟隔壁弄堂,今天黄河路这里的梅福里。当时汪康年、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、梁启超的同伴麦孟华也都住在这里。这些人就抱团去跟马氏兄弟学拉丁文。
这也影响了蔡元培。蔡元培1901年来到南洋公学,也带着学生跟马相伯学拉丁文。不过马相伯劝他说拉丁语在西洋也已是骨董了,不必人人都学。马相伯考察欧美学校的时候就注意到,受到近代科学文明的影响,学风已有转换。
马相伯还是第一个在大学开设哲学导论课的人,1903年震旦办起来之后他开了《致知浅说》,从西方古典哲学讲起。
马相伯参与的洋务、政治都失败了——他积极参政,给民国制定约法,没想到一夜之间回归帝制,到最后还是办教育最成功,教育才能够百年树人,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。
文汇报:他还庇护了于右任,发掘了陈垣?
李天纲:于右任年轻时候在家乡陕西关心国事,发表言论被追捕,是马相伯秘密收留他在震旦读书,他终身事马相伯为再生之父。陈垣与马相伯也是师生关系,马相伯很早就注意到陈垣。后来陈垣的好多研究都是马相伯定题目、帮他在徐家汇抄材料。陈垣自己也有独到之功,他不懂外文,就读《四库全书》。马相伯开一个题目叫《也里可温考》,陈垣做得非常好,成为他的成名作。解放后,陈垣与陈寅恪齐名,称“史学二陈”。
马相伯的教育思想里还有一点值得说。1912年,马相伯在严复之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第二任校长,他就任当天就说:“大学者,非以校舍大,学生年纪大及教习修金大,乃以学生有高等之程度及高尚之道德而大。”北大那时候有很多拖着不毕业的老学生,等着领津贴,吃喝玩乐、捧戏子等等,后来蔡元培也是依照马相伯的方向,整顿了风气。二十年后清华梅贻琦讲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,我觉得就是从马相伯这句话来的,只是马相伯讲得更务实、更切题。
“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”的选目,钱先生加了两种
文汇报:对马相伯的系统研究,是何时开始的?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马相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地位?
李天纲:马相伯的系统研究是朱维铮老师带着我们做的。1987年有一个中外比较教育的合作项目,有位加拿大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老师来做震旦和复旦的研究,自然地就开始研究马相伯。
当时只是捎带着研究马相伯,认为马相伯好像不那么重要,觉得19、20世纪之交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、章太炎。现在我们知道,马氏兄弟这两位“早期改良派”虽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前驱和潜流,但其实他们的造诣、思想能力和对中西文化的掌握,远超后面两三代人。
民国那一代读书渊博的人,其实是了解这些情况的。1986年三联书店准备做“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”,朱老师是主编,董秀玉总编辑请到钱锺书当名誉主编,拿了朱老师的选目给钱先生看,钱先生都很赞成,只是加了两种——《马氏兄弟文集》《辜鸿铭集》,朱老师也是欣然接受。
此后我一直在做马相伯的研究,后来就参与编辑了《马相伯集》,写了一篇专文,收入《马相伯传略》,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时已经单独成书。但那时候我觉得还没做完,就跟朱老师说要做年谱长编。我们也是一边做,一边才越来越意识到马相伯的重要性。原来只有一个很简单的《马相伯先生年谱》,是马相伯的小友张若谷,震旦、复旦时期马相伯教拉丁文的助手张乃昌的儿子,在马相伯百岁时仓促做成的。张若谷拿到商务,张元济当场就要出版。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素材。马相伯晚年,社会上对他的生平兴趣蔚然成风,因为他与世无争,讲话又说得很准,阅历又如此丰富,什么人都愿意到土山湾去找马相伯聊。有一本是高语罕化名为“王瑞霖”所作,叫作“一日一谈”,作为线索相当有用,但年代上需要订正。
文汇报:《马相伯年谱长编》有很多背景交代,结合各种史料,记述了包括江南地区屡次水灾台风、太平天国等近代史事,兼及家族成员事迹,包括弟弟马建忠,外甥朱志尧、朱开敏等;还记述了谱前谱后若干年的事件。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编纂时的考虑吗?
《马相伯年谱长编》(复旦大学出版社,2025)
李天纲:我最初想的是用年谱为传记收集资料,但做下来以后觉得一般的传记可以不写了,就用年谱长编来代替。我对马相伯的一些文献资料的收集、生平的查证,包括对马相伯的一些基本判断和思想价值的评述,就都放在长编里。我希望用年谱长编的体例来承担传记的功能。
年谱长编是中国学者做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体例,应该延续下去。我心里很喜欢的一部年谱长编是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,他们编得非常好,我非常受用,现在都扔不掉。
我将马相伯的家族成员、周围友朋的交游也放进去了。因为在查到线索之前,真的不知道,原来有些人的关系那么近,比如说段祺瑞下野后来上海,只拜见了马相伯、章太炎“二老”。还有,我们甚至找到辛亥和抗战期间都有特务盯着马相伯。这些都说明马相伯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对他人及政局的影响非常重要。
发布于:上海市配资实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